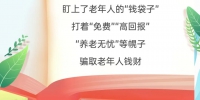林敏:群体性环境侵权特征、原因及对策研究
尤溪县检察院 林敏
一、群体性环境侵权的概念
近年来由大规模环境侵权引起的群体性环境维权事件时常发生,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个体化使一般的公众丧失了通过组织化渠道获得救济的能力,而通过行政、司法等手段的个体诉求往往得不到回应与解决,人们就越来越多地选择集体性抗争作为主张权利的主要手段,如浙江“海宁事件”( 2 0 1 1 ) 、大连“P X 事件”( 2 0 1 1 ) 、浙江“镇海事件”( 2 0 1 2 ) 等。
目前理论界并没有对大规模环境侵权作专门的定义,但大规模环境侵权是大规模侵权的一个重要类型,张新宝认为:大规模侵权是“被侵权人人数众多、损害后果严重影响重大的侵权事件,包括大规模产品责任事件、大规模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事件、大规模工业事故。”而群体性环境纠纷是群体性纠纷的一种,它是指“纠纷主体一方或者双方在多人以上特殊性社会纠纷;或者说一方或双方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相互之间坚持对某个法律价值物的公然对抗。”
群体性环境侵权行为是指一种人数众多,为求得同一问题解决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以一致行动寻求法律救济,造成一定后果的环境侵权新类型。该“同一问题”通常表现为“因环境遭受污染或破坏,从而使多数居民的身体权、财产权、环境权和其他权益遭到损害的事实”;“一定后果”通常表现为加重了对受害者权利和社会效果的损害。本文中的群体性环境侵权包涵“受害者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和“诉求的多样性和反复性”的特点,所以这里的“群体性”应被认为“因环境侵权形成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具有“对抗性”的一致行为导致了一定“破坏性后果”,“破坏性后果”通常是指加重了对受害者权利和社会效果的损害。
二、群体性环境侵权的特征
在法理上,环境维权抗争应当是某一区域或群体为维护自身环境利益而发动的集体维权行为,它的背后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公众的环境权利与国家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权威是相容的, 而不是相互抵触的。一般说来,公众的环境维权行为是以法律法规为框架和底线的克制行为, 而不是激进的有组织犯罪和泄愤行为。但是在民众情绪激动而申诉无门的情况下,群体性环境维权行动就有走向无序的可能。环境维权群体性行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1)所维护的利益有法律依据
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在总结中国社会群体性维权抗争的关键性特征时指出,“规则意识” 在中国是主导性因素。中国境内的社会抗争总是按照国家的规则进行,参与者随时关注国家放出的政策信号。李连江和欧博文也认为,中国的此类抗争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在环境维权群体性行动过程中,参与者积极运用国家的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利益免受污染排放企业、地方政府的侵害, 宣扬公认的正确理念和话语口号(如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关注民生等) 来支持己方的权利主张的合法性, 避免维权行动被贴上“ 非法集会” 等具有政治不当色彩的标签。事实上, 在很多的环境事件中, 公众的诉求基础要么是权利遭受侵害而未获得应有补偿, 要么是某一项目没有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进行信息公开、意见征集或环境影响评价,这种情况下的权利主张具有合法的依据。
(2)弱组织化或无组织聚集
一般而言,在中国,环境维权行动的组织化程度都很低。从经验观察可知, 那些由民间精英号召的或者由基层自治组织(如居民社区)主导的环境维权行动, 勉强可被称为典型的“弱组织” 型权利主张;除此之外的大部分环境维权抗争则呈现无组织的状态。这些无组织的维权行动大都是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来进行地区性动员, 进而将分散的个体汇集在一个共同的权利主张周围。这样的分散化维权行动虽然有利于避免陷人“组织化”的政治合法性困境, 但因缺少理性的组织与策略, 很容易超出法律的界限, 甚至走向“ 乌合之众”的情绪宣泄。正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所说,“当一个社会中各种成分缺乏有组织的集体,或者无法通过现存的有组织的集团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时,一个偶然的事件或一个领袖的出现都可能促发人们积蓄的不满, 并会以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发。”
(3)受害者的对抗性和破坏性
由于合理诉求得不到解决,损失得不到补偿,受害者往往组成暂时的利益共同体,采取一些激烈的行为方式寻求法律救助,例如静坐、冲击、游行、上访等,结果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公私财产损失。例如在“4•10”事件中,东阳市画水镇部分村民认为附近的“竹溪化工园区”对当地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在与当地政府、污染企业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采用搭建竹棚、设置路障等方式,阻止企业生产运输,迫使企业停工停产。市政府在了解情况后,组织多名公安、城管、运管以及社区干部、妇女主任等,来到东阳市画水镇,进行强制拆蓬、疏散、整顿。结果村民与执法人员发生重大冲突,造成 33 名执法人员和 3 名群众受伤住院,其中 5 名执法人员伤势严重,汽车被毁坏,经济损失巨大,还造成当地学校停课。这种对抗性和破坏性是近年环境侵权案件不断出现的新特点,其加重了对受害者权利和社会效益的损害。
(4)诉求的多样性和反复性
首先诉求的多样性是由受害者的复杂性决定的,受害者社会角色不同,文化素质各异,所以诉求的内容可能不同;其次,由于受害者对抗情绪的不断加强,参与者可能变得鱼龙混杂,一些并未受到损害的人们也可能参与其中,从而造成诉求的多样性。例如“7•16”中石油大连海域污染事件中,受损失的养殖户分批到北京上访,要求合理赔偿;在大连市海洋局拿出《“7•16”事故赔偿的征求意见稿》后,又以上访、信访等方式集体抗议。这一结果的发生除了因为赔偿方案不合理外,也与受害者的诉求多样性有关。诉求的反复性可能是由于赔偿不合理、不及时、不充分造成的。例如在“4•10”事件中,在镇政府的协调下,村民们在 3 年内还是获得了 38 万元的赔偿,但由于受污染的村民数量太多,分给每个村民只有几十元钱,完全无法弥补村民的损失,所以导致诉求不断。
三、环境侵权群体性行动的产生原因
(1)地方政府唯GDP的错误政绩观
对“增长是硬道理”、GDP 总量和增速的追求,使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极易形成“政商同盟”, 结成“权力一利益的结构之网”。特别是,在由中央政府掌握地方官员考核与晋升这一“治官权”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只有使本地经济快速发展才能在这种“晋升锦标赛”中获得政治发展空间。这促使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在经济和环境两个层面上呈现截然相反的目标诉求: 在经济发展方面“只有更好”,对环境保护却要求“没有最坏”。
(2)地方政府的消极处理态度
其次,地方政府消极回应群体性环境主张或无底线地压制环境维权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初始阶段,地方政府忽视、拖延和压制群体性环境权利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为了引起上一级政府的注意,公众开始选择具有宣示性和对抗性的集体对抗策略。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示范效应,固定了群体性环境权利主张所依赖的路径。2012 年发生的什邡事件、南通事件、宁波事件,都是在政府陷入信任危机之后,当地公众采取的群体性对抗策略,而从网络上的联动、宣传等趋势来看,这些事件具有很强的模仿性。
(3)表达、协商和纠纷化解机制的缺位
环境维权行动异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法律化的协商和利益维护机制。具体而言,其一,信息不公开阻塞了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协商渠道,使公众情绪极易被各种猜疑、谣言、传闻左右,埋下了矛盾激化的隐患。事实上,“什邡事件”和“宁波PX事件”都是由于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没有及时公布甚至谎报引发的。其二,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集会游行示威法》也声称以保障公民的上述权利为宗旨。但从后者的具体规定来看, 则是以“限制”为取向的。这样,合理的群体性环境权利主张, 极易转变为不合法的群体性事件。其三,权利救济机制的相对缺位或失效亦消解了公众借助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能力和机会。信访、行政复议、诉讼等正常的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机制频频失效, 群体性的权利主张和维权行为通常被阻截压制, 公众对体制内合法路径丧失了信心, 也只能诉诸于公开的、对抗的、体制外的措施, 希冀通过制造“声势”获得更上层权力机构的关注和救济。
四、环境维权群体性行动的对策研究
(1)拓展公众参与平台
包括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协商平台及信息公开平台。其一,建立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平台。政府与其他主体可以通过协商平台就环境事务交换意见,达成共识。政府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说明环境治理策略的理念、目的和具体运行方式,非政府主体可以就此提出建议。这种方式可以将共识建立在利益衡量和相互妥协之上,并使环境治理决策公开化,增强政府决策的正当性。其二,信息交换平台。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方式,是公众知情权实现的重要方式,亦是公众在环境侵害发生后维护自身权利以及积极有效地参与环境事件处理的前提。这种信息交换与公开可以提高政府在环境事务中的公信力,可以确保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等关键环节不走过场, 进而使政府之外的治理主体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信息传递的节点,增强参与者的活动能力。
(2)将分散的个体利益主张集合化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将个人从“单位”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具有自主意识和能力的新个体。更多的主体能够通过自己的知识、能力和理性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个体天生是独立自主和自我选择的行动者,在任何不对他人构成“伤害”的领域内享有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中, 高度分化的利益没有获得合理的组织化也是一种内在根源。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不在于抹杀公众的环境利益诉求, 独存企业与政府的利益, 而是应促进公众分散的利益集合表达。要允许依法建立的环境NGO存在, 发挥环境NGO的整合作用, 提升个体参与环境治理和权利救济的行动能力。并鼓励相关的NGO建立一整套关于决策、动员、管理、意见集成和权利主张的程序机制。
(3)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包括信访、行政复议、诉讼和替代性机制。为了防止环境权利主张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第一,应当完善信访制度, 既要改变现行信访工作考核以降低信访数量为标准的传统做法,也要建立有效的监督监察机制。第二,要健全完善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以维护公众权利、化解利益冲突和行政争议作为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将群体性利益争端化解在初始阶段, 防止行政权力在化解纠纷的过程中超越法律的框架,从而提高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第三,完善群体性环境权利的法律救济途径,提升法院在群体性纠纷解决中的作用。这既要提升法院司法权的独立性,赋予其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增强法院应对群体桂环境权利主张的能力,也要发挥律师在群体性环境权利主张中的专业优势,通过其与企业和政府之间专业化的沟通协商,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降至最低。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完善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并进一步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第四,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建立专门针对群体性事件的人民调解、社区调解、司法调解、第三方仲裁、专门委员会磋商等机制。